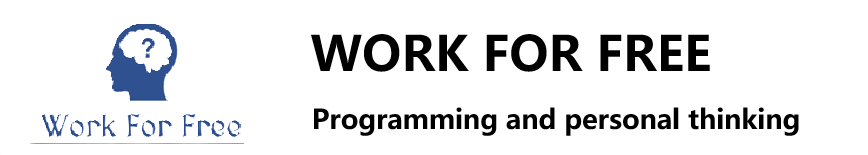凤鸣山问丹
上虞的秋日,凤鸣山薄雾如纱。我沿石阶缓步而上,两旁古木参天,溪水泠泠作响,仿佛仍回荡着千年前炉火噼啪的余音。山腰处,一方“炼丹井”静卧于苔痕斑驳的石栏内,井水幽深,映不出魏伯阳的身影,却照见自己模糊的轮廓——这方寸水土,曾是他与弟子们埋首炼丹、叩问长生的地方。
山间传说里,魏伯阳炼成金丹后,以犬试药,犬倒地如死。两位弟子心生疑惧,弃丹而去;唯有一人笃信师道,愿同服共死。结果师徒与犬皆复苏飞升,而犹豫者终老山下。故事如山风拂过耳际,初听是仙迹,细思却如井水般冰凉:那“坚定”的信念,究竟该交付给谁?若丹本为毒,那“信”岂非成了引向深渊的绳索?
下山途中,偶遇一位老农在田埂上歇息。他笑谈:“如今谁还信什么金丹?但人总得信点什么吧,不然日子怎么过?”他信的是节气、是土地、是春种秋收的踏实。这朴素之“尚”,与魏伯阳的玄奥丹道相隔千年,却同样支撑着一种生活。吴晗先生曾言,社会风气之“尚”如潮汐涨落,或尚名节,或尚功利,或尚清谈——可无论何种“尚”,若只知随波逐流,不加省察,便如那两位弃丹弟子,既失了飞升之机,也未必真得了安稳。
归途车窗外,城市灯火渐次亮起,霓虹如新的“丹炉”,闪烁着财富、流量、速度的诱人光泽。我们这一代人,何尝不在各自的时代“炼丹”?只是炉中所炼,早已不是铅汞,而是对意义、价值与归属的渴求。然而,若只知追逐那最耀眼的光,却不肯停下脚步自问一句“此丹可服否?”,恐怕终将陷入另一种“假死”——身体活着,灵魂却已沉睡。
凤鸣山无凤鸣,唯有风过林梢。魏伯阳的丹炉早已冷透,但那口炼丹井却像一面古镜,照见所有时代人心深处的叩问:我们该信什么?又为何而信?
苏格拉底说:“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。”或许真正的“丹”,并非服食之物,而是那敢于审视自身信念的勇气——它不许诺飞升,却能让双脚在尘世站得更稳,让眼睛在迷雾中看得更清。